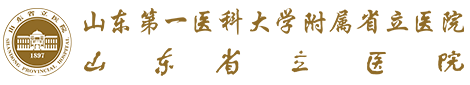从纳兰词说开去
“风丝袅,水浸碧天清晓。一镜湿云清未了,雨晴春草草。梦里轻螺谁扫。帘外落花红小。独睡起来情悄悄,寄愁何处好?”
纳兰词,清澈如水。作者纳兰性德,字容若,号楞伽山人。自清以来,他那词里所表现出的清婉凄恻的意境,拨动了多少少年儿女的情怀。梁启超曾评论他:“当时一位权相明珠的儿子,是独一无二的一位阔公子,他父母又很钟爱他;……说他无病呻吟,的确不是。他受不过环境的压迫,三十多岁便死了。所以批评这个人只能用两句旧话说:古之伤心人,别有怀抱。”陈其年将他和南唐李后主相提并论,王国维先生更认为他的词不但是清代第一人,而且是宋代以后第一人。
纳兰容若为什么会写出《饮水集》那样的词来?那些词一片悲恻凄婉情调,不是追忆往昔,便是感慨今朝,十有九首都是痛苦的倾诉,凄怆的呻吟,如果不知道他的生平,一定以为他是穷愁潦倒的文人。然而,他却是权倾一时的相国明珠的公子,二十一岁中进士,官至通议大夫,一等待卫,连皇帝都宠爱他。那个年代,他的身世,他的地位,足可光宗耀祖。许多人将纳兰容若与李后主相比,可是李后主词的那些悲苦音律,都是在他成为阶下囚之后写的,在此之前却是充满了个人欢乐。但纳兰容若一生几乎没受过什么波折,为什么他的词会那样悲苦呢?天上人间情一诺。回首何处玉人影。是回廊曲处?是灯下呵手?曾经共弄丝柳,共擎画轴。满纸的哀愁,单单是为了青梅竹马的卢氏吗?少年知己,一入宫门杳无迹,这是彻骨的痛。三年后,相知相爱的妻子又弃他而去,如何不叫他心字已成灰,愁痕满地?
诗词之道,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林妹妹之口说过:无非是些起转承合,如果立意词句都新奇了,连格律都可以不守的,调子太孤寒凄清了,诗词便落了下乘。林妹妹说了个“冷月葬花魂”,心直口快的湘云赞了好之后,说太悲了,对你不好。一阙“葬花词”听得宝玉五内俱焚,更是从那泣血般的句子里感到隐隐的不祥之兆。
苏轼因乌台诗案,被发配到蛮荒之地,“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每无炭,夏无寒泉”,他尚以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自宽;辛弃疾在感叹大江东去之余,仍不失壮怀激烈;李煜国破家亡才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”;李清照一介女流,在孤身南渡的颠沛流离中,也不过是“风鬟雾鬓,怕见夜间出去”……她在《词论》中说:“五代干戈,四海瓜分豆剖,斯文道息。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,故有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、“吹皱一池春水”之词。语虽甚奇,所谓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也。”南渡之后,国破家亡,李清照的词作也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,充满了凄凉低沉的家国之痛!
文学作品的优劣,首先是作品对社会生活或人类情感的反映深度;其次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作者的独特的个性;再次是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。品赏一篇文学作品,最根本的是看作者表达的思想内容,和作者通过语言所表达的艺术境界,文学不是思辨的科学,而是形象思维的“人学”。如果一篇作品一味沉浸在个人的情感、得失、忧郁之中,即使词藻华美,那也便落了下乘。好的作品,不必辞藻华美,不必气势恢宏,也不必长篇大论,只要能揭开生活一角,带有生活中的某些普遍性,能引起读者共鸣,即使截取生活中一个片段,那怕寥寥数语,也不失一篇美文。